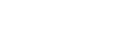关于李樯
李樯,1968年生人,著名编剧,主要影视作品《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好想好想谈恋爱》,话剧《穷爸爸、富爸爸》、《小王子》等,第6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编剧得主,剧作图书《孔雀》、《立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本月上架。
手 记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本也出书了,就知道找到李樯已经不是件容易事儿了。看着李樯参加新书发布会、看着李樯回答记者提问、看着李樯签售、看着李樯跟影迷合影,直到看着李樯头顶上冒着热气,却腰板儿笔直地坐在我旁边,采访才开始。后面有通告等着、门口有媒体等着、外面有读者等着,我和李樯坐在了一个角落里,享受片刻安静,这种安静的对话自从电影上映和新书上市开始就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对于等了他4个小时的我,他挺歉意,对于他还不能休息,我也歉意。默契到只寒暄了一句,我问他:“能习惯吗?”他像个没松劲儿的发条:“还好,还好。”
都说李樯温文尔雅,我看不见得,“尔雅”没问题,恭谦礼让,仪表上一丝不苟,“文”字也不为过,举手投足间尽是学人气质。而“温”却就是假象了,赵薇说他内心有火山,我看形容得恰到好处,表面的平静只为了等待灵感的喷薄,他的剧本中拥有足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感到共鸣、感到欢乐、感到悲伤、感到虐心、感到释然的内容,他将作家的故事改编成你似曾相识的回忆和潜意识中的未来,他诠释了好文字也可以属于职业编剧,他骄傲:“我就是个编剧。”
19岁北京军区入伍,做了一名文艺兵,22岁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25岁毕业分配进入战友话剧团担任编剧,两年后开始做职业编剧。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他在与生活的斗争中积蓄灵感,在理想和现实的撕裂间找寻平衡,安逸还是冒险?执著还是放弃?留北京还是回老家?十年后,他编剧的《孔雀》拿下银熊奖,成就了顾长卫的同时,李樯也为自己的坚持找到了答案。2013年4月,在李樯的撮合下,他与关锦鹏一起帮助赵薇完成了毕业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剧本比电影完整 人性没有进化论
新报:国人其实并不大习惯看剧作图书,而且此时出书还有炒作之嫌,你却一次出版了三本。
李樯:我之前的剧本被拍成电影之后,很多人跟我要电影的原剧本,网上也流传着关于《孔雀》剧本的各种版本,但是那些剧本比较乱,并不是我的原版。电影本身的放映时间有一定的限制,会对剧本进行部分删减,所以很多人会对剧本变成电影之前的样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它原本的面目,于是我就将它们出版了,很自然的事儿。
新报:《立春》、《孔雀》、《致青春》三个不同时代的青春故事,对你来说,青春变化了吗?
李樯:每一个时期的年轻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是不同的,每个时间段的年轻人都有他们在那个阶段里所特有的一些精神风貌。想捕捉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状态,就必须捕捉专属于那个时代的特质。其实探讨不同时期的青年人,就是探讨不同时期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人就是时代的尾随者。时代永远在变化,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但是人性中是没有什么进化论的,这是我的看法。
新报: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那将来的作品会涉及什么题材?
李樯:我在写《放浪记》,我想写得比之前更好一点儿。慢慢来吧,我想很多题材我都会去尝试。
内心少不了狂野 主流性格充满热望
新报:听说你当过文艺兵,当时的生活重心就是唱歌、跳舞,很难看出来你有这段经历。
李樯:人都是多样性的。
新报:赵薇说你是“狮子王”,内心有特别狂野的一面。
李樯:当然有狂野的一面。每个人都是多层面的,主流的性格不代表人只有一面。
新报:狂野、内敛、激情、热望四个词挑选一个来概括你的主流性格。
李樯:我选择热望。因为我的很多作品都在谈论理想,理想是我作品中从没逝去过的一个主基调。
新报:听说你当过北漂,很长的时间都在迷茫,怎么看那段日子?
李樯: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藏。最难受的东西未见得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未见得是好受的。我觉得现在每天可能都在历练自己。
新报:经历了这么多磨砺,你觉得自己更容易被感动还是更容易在日子里找到平静?会不会反映在剧本里?
李樯:我觉得不同的感觉给我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东西在起伏,是我内心的起伏,你对生活的观察是带有你主观折射的,生活里本来就没有真正客观的东西存在。好的剧作家都是冷静的、间离的、客观的。
钟情菜市场 总写女人是巧合
新报:你的作品会写出让人觉得撕心裂肺的真实,你怎么去完成你对生活的观察?
李樯:作为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我就在感受着我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风向标,我感受着生活给予我的东西。我是怎么感受生活的,我就怎么写。
新报:之前看《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都是小城市中的故事,而且你总是把重头戏放到菜市场上,难道你对菜市场有独特的感情?
李樯:我真的对菜市场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场所,菜市场有着对生活最基本、最朴素的依赖与要求。每次走进菜市场,我都觉得那是最能裸露生活面目的地方,里面有一种生生不息、孜孜不倦的对生活的渴望。我本身出生在小城市,所以小城市那样的生活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其实多数人是在小城市里面长大的,毕竟大城市就那么几个,所以小城市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样貌。
新报:为什么你剧本中的主角都是女人?男人怎么写女人?怎么观察女人?
李樯:我没有去特意观察女人,我觉得男人女人都一样。对我来说,“恰巧”这几部的主人公都是女人,不排除以后作品的主人公会是男人,主人公都是女人并不是我刻意完成的。我想我一生的写作周期会很长,这大概是一个阶段呈现出的东西吧。
改编不是偷懒 是不是作家不重要
新报:很多人在拿你的改编剧本跟辛夷坞的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对比,很多人觉得改编是一件偷懒的事儿。
李樯:原创剧本就像自我生长的一株树,而改编剧本则像是一次嫁接过程。我在改编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不是说塑造几个不同的人物,而是如何将小说里面男女主人公那种一对一的局面改编成一种众生相。其实原创和改编都不容易,都不省力气。
新报:电影剧本的编写不同于电视剧,导演的要求会非常多,你得按照导演的要求写剧本,拍摄的时候导演甚至会二度创作。你和赵薇之间的冲突大不大?
李樯:你说得对,不过赵薇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她的这部戏不想要男女之间唧唧歪歪那种感觉,她想拍得有时代感,这与我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所以对原作改动得比较大,是二度创作。到了拍摄的时候也很顺利,基本上完成了剧本95%的样子。
新报:有没有对你影响深刻的作家和作品?
李樯:很多很多作品给过我深刻的影响,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契科夫、福克纳,还有《红楼梦》,很多很多,不胜枚举。电影也有很多,电影是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在我生活中最常见的。
新报:平时喜欢做什么?
李樯:阅读和观赏。会看很多戏剧、话剧。话剧和电影对我来说都一样,必不可少。
新报:你现在也出书了,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吗?
李樯:这个称呼不重要,其实我就是一个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