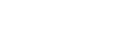经卷修复前
经卷修复后
经卷修复中
潘美娣
登科录二修复前
登科录二修复后
从18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至今,潘美娣与“受伤”的古籍打交道有50个年头了。现在,她还兼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的特聘古籍修复专家。
在中大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见到潘美娣,才发现,这项日复一日颇显枯燥单调的工作赋予了她更高层次的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含蓄蕴藉之气。她笑称这是个修身养性的职业,她以前性子很急,现在则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不疾不徐、不温不火。跟她聊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搓纸钉搓出个人“招牌”
1963年,潘美娣进了上海图书馆,一去就被安排做古籍修复。“那时候的人心思单纯,被安排做什么,都毫无条件地答应。”当时,全国就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大图书馆有专业修复人员。“古籍修复根据地方气候条件不同,有南北派之分。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而北方的古籍,因为气候干燥,风化、焦脆的比较多,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而潘美娣的师傅曹有福,可以说是南派中的高手。
进图书馆的第一天,领导将潘美娣带到了曹有福的面前,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她并不满足,暗自琢磨:“为什么师傅搓出来的能那么细致?”靠着心去领悟,靠着手去调整,一个下午过去,潘美娣的手都搓僵硬了,但她也一句话都没说。最后,是曹有福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已有半抽屉多。
“师傅采用的是很传统的带徒弟方式,他不讲什么理论,也不会给太多指导,只告诉你一条基本的原则:古籍修复必须整旧如旧,不能一本旧书过手后,变成一本新书,那绝对是大忌。其他的所有流程,师傅示范一遍,你就按着去做,做得好与坏,师傅看在眼里,也不会多说,主要靠自己琢磨。但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诱惑,人更能沉下心来,所以往往能更快地上手。”潘美娣感慨,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她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第一印象就挺好。这犹如一个人的招牌,拿出来好与坏,一目了然。”
两年后学成归来,潘美娣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她强调的是,自己赶上一个好时代。“那时候老先生们都还在,他们视书如命。像顾廷龙馆长,对修复很重视,我们组里有十个人左右,每个人每次修完一批书,他都会一一过目。”后来,顾廷龙对管库的同事明确表示:“以后馆里面的等级藏品,都交给小潘修。”彼时,潘美娣也就二十多岁。
顾廷龙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言,潘美娣更是印象深刻——“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当时,馆里面有一本宋元时期的刻本,前人已经修过一次,但又烂了。重修时,我把它整个书页展开以后,书口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顾先生一看非常高兴,他的兴奋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自创“夹揭法”修复明代古籍
潘美娣特别强调,做好古籍修复得有“三心”:信心、耐心和责任心。“如果没有责任心,书页一揭不开就放弃了,那损失不可计量。况且,古籍修复是急不出来的,必须每一页打开后,一个洞一个洞地补,一本书可能要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一套书有十本二十本,一整年都搭进去了可能还弄不完。性子再急,一坐到古籍面前,人就必须平静下来。”
有一段时间上海图书馆要影印《永乐大典》,那必须整本拆下来,有坏掉的书页,先修好,再拿去拍照制版,回来后又要还原为明朝时期的硬包被装帧样式。《永乐大典》是馆里面的等级藏品,必须尽快弄完回库,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加班加点。
1972年,上海博物馆来了一套从嘉定明墓出土的唱本。这套书是陪葬品,与墓主的尸身放在了一起,几百年下来,已经被尸体腐烂后的血水浸泡得成了硬邦邦的书砖了。因为上海博物馆没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就到上图求借。顾廷龙很快派了潘美娣到上博去,同时去“支援”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先生。“由于这些古唱本都已变成砖块了,如果硬揭,必坏无疑,所以要放到蒸锅里去蒸,就像蒸包子一样,让其软化,才能一沓一沓地揭开,再一页页地细揭。还必须马上揭,冷了又会变硬,比原来还硬。因此,我们是能做多少就蒸多少。这一套书,我们两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修完。”
可见,古籍修复要根据每一套书不同的“受伤”情况制定具体的修复方案,甚至还要因书制宜地创造一些新办法,像“夹揭法”就是潘美娣的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太仓一座明墓里出土了一批古书,被送到上海博物馆,他们照例找顾廷龙,将这批古书送到了上海图书馆来修复。“太仓出土的这批书,有的书页看起来比较厚,实际上里面还有好几层,被黏在了一起,根本揭不开。于是我自己想了个土办法,在‘厚页’的两面各用浆糊再贴上两层纸,然后通过这两层纸的拉力将中间的书页一层层揭开,再清洗掉浆糊。”潘美娣晃了晃手中的《广州日报》,继续说:“任何一张报纸,中间都有厚度,我都可以一揭为二。”
事实上,以前的古籍修复工具都非常简单,一支毛笔、一瓶浆糊,就是所有配备。“以前都是自己想办法,需要用什么就做什么。现在裁纸有美工刀,以前哪有?都是马蹄刀,要自己磨刀。师傅告诉你怎么磨,你就好好干去。声音不对,师傅马上会说:‘你这样好像没吃饭’。以前也没有切纸机,做‘金镶玉’做完后,要切书,就自己用大刀来切。现在有机器辅助,省了不少力气。”
另外,古籍修复过程中,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配纸。首先是配大类,皮纸的书要配皮纸,竹纸的书要配竹纸,然后要测纸张的厚薄,现在有卡表,可以直接测量,以前就是凭感觉,事事都要更用心。
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
历来修书人的地位都不怎么高。传统的大藏书家往往会养一个修书人,却以“修书匠”视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块的重视也不够,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不太高,起点比较低。但古籍修复人员的作用就像调味料一样,少了还不行。潘美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皇家博物馆到北京邀请专家前往伦敦帮忙修缮中国古籍善本,当时老师傅们的年纪都很大了,他们推荐到上海图书馆来找人,但那时候出国是一件大事,图书馆方面最后以“技术保密”为由将人家打发走了。到了80年代后期,法国一家博物馆因为不懂修复,将收藏的一批受损的中国古籍一页页拆下来,封进了薄膜里面,令这些书彻底完蛋。通过这次教训,国内外在古籍修复方面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国家对古籍修复也日渐重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没成立之前,全国比较有水平的修复人员不足百人。在举办过的15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中,参与培训的大概有五六百人。回去真正从事古籍修复的,虽然没那么多,但总比以前好多了。”同时,大专院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像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学院都有古籍修复专业。目前,中山大学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而中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就是潘美娣和同事一起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中心最里面的那个房间中,两排架子上叠放着各种各样的手工纸,那是潘美娣2003年到江浙一带订制回来的,足够用几十年。
“我们总说民国时期的书籍难以保存,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正是从手工造纸到工业造纸的过渡期,机械化程度不高,技术比较落后,添加的东西又多,结果纸的寿命很短。一般民国时期的报纸保存年限为60年,期刊杂志能存100年,好一些的书籍保存两百年估计也就到顶了。相反,宋版书如果保存得当,纸张放到今天都跟新的一样。因为当时是纯手工造纸,将树皮放在山沟沟的小河中泡、洗,腐烂成浆,不讲效率,也不计成本,添加的东西少,所以纸张非常好。现在添加很多化学物质加速腐化,出来的纸质量远不如前。所以,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她们专程到安徽找宣纸,到江浙找皮纸,即便在当年非典时期,潘美娣和同事也若无其事,一门心思都在寻找好纸上。
大家简介
潘美娣,1963年进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与装帧工作。曾师从曹有福、张士达、肖振棠等古籍修复前辈。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古籍修复专家。多次担任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授课教师;并为江苏省文化厅纸浆补书技术项目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莫愁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