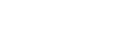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和刻本和道光刻本《清嘉录》
刘云,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古籍保管员、副研究馆员,从事天一阁所藏古籍的管理、编目和整理工作。发表论文有《清代宁波书坊刻书考》《民国期间宁波印刷业考述》《天一阁博物馆馆藏和刻本述略》等。与人合著《天一阁藏清代珍稀稿本提要》。
天一阁藏“和刻本”内涵丰富
什么是“和刻本”?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刘云解释:“和刻本是指日本翻刻的中国书籍和日本人编撰刊刻的具有中国古籍特征的书籍的统称。有的和刻本有日文注读。”
和刻本与中国古籍如何区分?刘云认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纸张,日本的和纸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纤维较长,但透明度较高,所以从背面看,一些和刻本的字迹会透出来;其次是看封皮,和刻本的封皮大多比中国古籍要厚,并且有些经过染色处理,有淡蓝色、黄色、米黄色或者砖红色等,整体比较淡雅。当然,和刻本基本上也采用线装形式,和中国古籍外观上差别不是很大。
关于和刻本,早在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就有记载,晚清民国时期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记》和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也有著录和记载,为研究中日图书交流提供了大量材料。特别是叶德辉编纂的《书林清话》,第一次对日本、朝鲜活字版做了总结性的研究。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和长泽孝三合著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近年来,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刻本研究也走向了深入。1995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收录北京图书馆等大陆68家公共、大学图书馆庋藏的日本1912年以前刻印、抄写和校注的中国古籍3000余种,对了解和刻本汉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一阁的和刻本从何而来?刘云介绍,天一阁的和刻本主要来源于宁波地方藏书家的捐赠,加上其他各种途径而来的新藏书,共180多种。其中包括甬上藏书家朱赞卿的旧藏69种,冯贞群旧藏27种,张季言樵斋旧藏8种,孙家溎蜗寄庐旧藏8种,杨容林清防阁旧藏4种,还有甬上著名中医徐余藻所捐医学文献5种。
天一阁藏和刻本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翻印、刊刻出版的书籍为主,其中时间最早的是日本宽永二十年(1644年)译田庄左卫门刊刻的《武经七书直解》十二卷,最晚的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相当于整个清朝时期。这些书涉及日本重要的书坊,如江户嵩山房、浪华书肆、玉枝轩等。
和刻本分两种,一种是和刻汉籍,即日本翻刻、重刻中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书都有。另一种是用汉文字书写并刊刻的日本人著作。
天一阁藏和刻汉籍比较丰富。经部文献,从《周礼》到《春秋经传集解》都有。至于史部文献,日本人特别喜欢有借鉴意义的,有《通鉴纪事本末》《唐鉴》《名臣言行录》《灜环志略》等书。子部文献,大部分为医学文献,唐宋金元明清时代的代表性医学著作有16种,可见日本在借鉴中国医学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同时,日本又是非常崇尚武士道的国家,故对兵学文献也非常重视,像《赵注孙子》《武经七书》等都有刊刻流传。日本是汉文化圈国家之一,他们也十分重视儒家文献的刊刻。天一阁藏和刻本儒家类文献有《臣轨》《群书治要》《贞观政要》三种。像这些书在中国国内长期失传,但在日本竟然保存得非常完好。集部文献9种,包括《陶渊明集》《唐王右丞诗集》、李攀龙《唐诗选》《柳文》、清林云铭撰《楚辞灯》等。特别是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形成日本人中国文学修养和趣味之重要部分”的一部书。
除了刊刻中国典籍,天一阁藏日本人编撰刊刻的著作有31种。刘云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类是日本人整理研究中国文献的著作;第二类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为了向西方学习而编撰的西方历史的著作;第三类是日本的汉文诗文;第四类是日本人编纂的画谱和书法;第五类是日本人撰写的小说类的作品,如长田偶得的《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菅原忠俊的《菅家书则清演义》。其中天一阁所藏《菅家书则清演义》是日本文化七年(1810年)原刻本。而《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曾在晚清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激励作用。
中日书籍交流快速双向
中日书籍交流之快速,令人称奇。刘云举例说:《宋朱晦庵先生名臣言行录》为崇祯十一年(1638年)古吴张采刊刻,29年后,日本风月庄左卫门翻刻行世;天一阁藏有日本元禄十年(1697年)柳枝轩刻本《韵府古篆汇选》五卷,是覆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武林陈氏刻本,两者仅相隔25年;日本弘化二年(1845年)修道馆刻本《韩非子》,则是根据清顾广圻覆刻宋乾道本再刻的,时隔27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墨海书馆铅印出版了《地理全志》五卷首一卷,咸丰四年(1854年)又雕版印刷了下编十卷。四年后,日本就出版了全套《地理全志》。刘云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即便如此,中日书籍的交流速度还是很快的。只要20年左右时间,中国出的书在日本就有刊刻行世。我所依据的还只是天一阁的藏品,如果放眼全国,说不定时间还能缩短。”
最能体现中日书籍交流速度的是《清嘉录》。刘云介绍,它是清顾禄撰写的有关江南岁时风俗的著作,道光十年(1830年)中国首刻,次年3月已经在东京书肆售卖,在日本广受欢迎。七年之后,《清嘉录》在日本翻刻行世。书前有序,详细地介绍了该书在日流传及中日书籍交流情况,所以它是中日图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书籍的交流是双向的。日本保存了好多中国的典籍,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些典籍在中国逐渐失传,在日本竟然还有保存。日本人对其进行了整理,最有名的就是《佚存丛书》。此外,还有《全唐诗逸》,同样也是早期日藏汉籍回归的典型。
“关于中日书籍交流,背后的故事还是蛮多的。比如,明宋应星撰有《天工开物》一书。第一次刊刻是在明崇祯年间,朋友涂氏为其刊刻的,清初福建商人杨素卿以涂本为底本翻刻了第二版,传到日本。日本本草学家见原益轩在《花谱》和《菜谱》参考书目中列举了此书。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菅原堂主人)发行刊刻了此书。1783年传入朝鲜。《天工开物》里提到了很多采矿、铸钱之法,并有违规之语,所以这部书在清乾隆时遭禁。虽在《古今图书集成》里记有部分内容,然而并不全。也就是说,后来中国流传的《天工开物》的各个本子,都是从日本影印过来的。没有日藏汉籍回归,国内很难见到这部书的全貌。”刘云介绍。
《一切经音义》的流传也非常有意思。有两部《一切经音义》,其一是一百卷的,由唐代释慧琳所撰;其二是流传比较多的二十五卷本,由唐释玄(元)应所撰。清代阮元在《四库未收书提要》中说,一百卷的《一切经音义》已失传。其实,他不知此书在日本是有传世的,而日本的刻本竟然是从高丽传入的。一部《一切经音义》,就能看出东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概况。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自古和日本交流频繁,从天一阁所藏和刻本,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交流的很多侧面。刘云说:“日本不仅接受了中国汉文字的书写方式,还接受了中国汉文书籍的阅读方式和汉文书籍的刊刻方式;从更深层面来讲,日本不仅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接受并效仿了中国士大夫诗文唱和的风雅生活方式;特别是明治以来,日本人研究汉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有意思的是,通过海上书籍之路,通过文化交流,中日两国在寻求政治变革的历史大潮中也互有借鉴。”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座。)
【文章来源:中国宁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