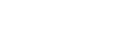陈佐湟 (中)在一次演出活动中。
2013年6月22日,陈佐湟的身影刚出现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伴奏乐池的指挥台上,观众席立刻响起热烈掌声。在大剧院原创歌剧《西施》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不少观众始终身体前倾,仔细倾听,或紧张,或舒展,大家似乎能触摸到音乐的呼吸。一位一直对高雅音乐敬而远之的年轻人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第一次觉得,“指挥是一个乐队的灵魂”这句话是那么传神。
可就在11年前,同样是陈佐湟担任指挥的一场演出中,一位迟到的女观众硬闯入席,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乐团成员怒目而视,陈佐湟忍住了没回头。第一乐章结束时,观众席上传出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迟到的观众则涌进来,乒乒乓乓地找起了座位……
陈佐湟,这位新中国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被世界乐坛誉为“小泽征尔之后最重要的亚裔指挥家”,认为自己最值得说的经历,就是“亲历了近30年来,中国音乐环境的巨大变化”。
6月盛夏,北京烈日和暴雨轮流登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陈佐湟位于国家大剧院4层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专访时,外面正是大雨倾盆。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谦逊平和、温文尔雅,可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只要谈到专业问题,他从不给自己设限,也从不介意自己的话会驳了谁的面子、揭了谁的短——就像夏天的雨,热烈得毫不掩饰。
文化上的失落是要还债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人和音乐,尤其是交响乐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陈佐湟:音乐是被时间积淀下来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反应,是人感情世界角角落落的一面镜子。作曲家将自己不同层次的情绪,从淡淡的忧愁到极度的欢乐都放到音符背后。指挥、乐队成员还有听众,就在这个感情世界里和这种情绪相遇、对话。这是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环球人物杂志:可现在能打动我们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少?
陈佐湟:那是因为有一些作曲家只是在为自己写东西,或者只是在进行一种音响上的实验,并不太顾及听众的感受。还有一些迎合某种要求创作的作品,演完一遍后就无人问津了。这都是很让人悲哀的现实。能怪观众不喜欢他们、不懂他们吗?绝对不能!音乐家们应该自责和深思的,是自己的创作目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当代艺术中,不少画家的作品都赢得了可观的市场回报,相比之下,音乐家的生存空间似乎没那么大。是市场对音乐家太苛刻吗?
陈佐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体裁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文学和美术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形态,可触摸、可再视,但音乐是转瞬即逝的。尤其是交响乐,没有歌词、人物形象等因素的辅佐,人们对它的捕捉难度,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上,都会更大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交响乐至今仍然比较小众的原因?
陈佐湟:古往今来,在任何国家,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从来都不是停留在统一层次的。不同的音乐形式有不同的市场、听众,我觉得这无需苛求。如果有一天交响乐变得大众了,那它就是流行音乐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听流行歌曲、看小人书的人,全世界都有,我不反对。但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小人书而没有《红楼梦》,我相信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
环球人物杂志:10多年前您曾说,“很多事情已经离音乐和艺术太远了”。如今再看,中国音乐的大环境是否已经纯粹了许多?
陈佐湟:可能是我的心太切,我觉得艺术生存环境的改变速度还不如艺术本身改变得快。我国一位很著名的音乐家曾对我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音乐了,只有音乐活动”。对于他的这种着急,我感同身受。比如,一些人把音乐当成沽名钓誉的手段,音乐本身的文化意义反而退居次要了,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搞艺术的人,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是做出最好的艺术产品。再比如,把娱乐和艺术这两个概念混成一锅粥。我记得我留学时曾问过老师:“全世界哪个交响乐团是赚钱的?”结果他瞪了我一眼,“如果有这么个乐团,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了”。后来我才知道,搞交响乐永远不可能赚钱。我们现在笼统地号召“艺术要走市场”,本身就有问题。还比如,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不少很有才华的音乐家渐渐开始浑水摸鱼。这些,都让我觉得很可惜。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有人说,当今社会陷入了经济发展、文化失落的怪圈。
陈佐湟:的确。难道生活好了,GDP增长了,我们就是大国了?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文化上的事情呢?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上的失落是要还债的,甚至可能不止一代人来还。
普罗米修斯偷火种
陈佐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没有音乐,自己这一生会是什么样?答案总是:简直难以想象。
上海的南昌路,是1947年陈佐湟出生的地方。这个大家庭里曾走出过不少名人:他的大伯是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父亲是爱国作家陈汝惠,哥哥陈佐洱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堂哥陈佳洱是前北京大学校长,母亲则是大学俄语教师……用陈佐湟自己的话说,“家里做什么工作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做音乐的”,他自己则完全是在一系列偶然中走上了古典音乐这条路。
1952年,因为父母调到厦门大学任教,正在读小学的陈佐湟也随着他们搬到了鼓浪屿。“岛上的音乐传统特别深厚,有钢琴的家庭特别多。”放学路上,陈佐湟总能听见路边窗户里飘出的悠扬琴声,虽然不太懂,却常常踮着脚尖在窗台下听得入神,忘了回家。“那时候,家里没条件买钢琴,妈妈就和邻居商量,租他们家的钢琴,每天让我过去练一个小时。”再后来,陈佐湟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在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43号大院里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
然而这条路,很快因为“文革”而中断。中学刚毕业,他就因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到了石家庄的郊区。开荒、插秧、收割,在那里的每一天,陈佐湟和同伴们都过着远离音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渐渐地,有人觉得生命中不会再有音乐了,但陈佐湟执拗极了,每天晚上伙伴们睡着后,他会趴在铺上,打着手电筒抄写借来的乐谱,学配器、做和声习题。
间或,他还坐上火车去找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上课。“记得那时候郑老师被下放到演样板戏的京剧团,我通过朋友介绍去向她拜师学艺,她问我:‘是想学点手上的活,还是想认认真真地学指挥?’我回答:‘当然是想认真学指挥。’于是,她就收下了我这个学生。”由于身处特殊年代,不能弹琴、不能出声,陈佐湟就把曲谱背下来,在郑小瑛面前无声地比划。
“也有人跟我说,‘你这样,最后会非常失望,因为你连回北京都不可能,更别提再做音乐了’。但我总觉得,只要临死时回想起来,我没有像你们一样打牌、抓蛤蟆煮着吃,而是看书了、自修了,我应该不会后悔吧。”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在正常的音乐训练被切断了整整12年后,陈佐湟终于重新回到了课堂。因为已经30岁,是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又是北京考区“状元”,陈佐湟成了作曲班的班长。在这个班里,有日后对世界交响乐坛产生巨大影响的谭盾、陈其钢等许多名家。
进校后,陈佐湟只用了一年半,就修完了指挥和作曲系的所有课程。1981年夏,他应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邀请,赴美国著名的坦格乌德音乐中心及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学习。
“我还记得,和我乘坐同一架航班的人中间,99%是访问学者,基本上是学医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等,一说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没有。坐在飞机上,我的心里真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火种的感觉。出去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把我们最缺的东西带回来。”
初到美国,陈佐湟英文很差,更别说教授在课堂上列举的一些作品,他甚至都没听说过。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把自己“锁”在图书馆。就这样,1982年,他拿到了音乐硕士学位,3年后又获得密歇根大学建校百余年来颁发的第一个乐队指挥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成了新中国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
此后,他先后出任美国威切塔乐团音乐总监、美国罗德岛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等职,在4个国家的8个职业乐团担任过音乐总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在中国音乐界,陈佐湟创下了几个“第一”:除了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他还是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位艺术总监、第一位在我国引进了音乐季制度的人,被称为中国交响乐改革第一人。
1987年,陈佐湟担任中国中央乐团指挥,带领中央乐团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24个城市做访问演出。这是新中国的演奏家们首次在海外大规模亮相。
1993年,陈佐湟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自述文中提到,中国的音乐家其实早已在交响乐这块欧洲人的“世袭领地”上表现出非凡实力,却往往要在国外出了名才会得到承认。怎样才能让他们在国内有更多的机会充分地展示才华?机会在3年后来到陈佐湟面前。1996年,他拒绝了美国乐团的高薪续聘合约,受聘回到北京,在原中央乐团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交响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
在陈佐湟的坚持与带领下,乐团在4年间共演出了255场音乐会,与宝丽金唱片公司(今环球唱片)合作录制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唱片在全世界发行,还出访了德、英等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亚洲一流的交响乐团。
然而,在这期间,陈佐湟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让他头疼的都是和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从钱到人事,再到生存环境等。“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音乐反而变成了最容易、最简单的事情。”
2000年,面对无序的竞争及巨大的生存压力,“国交”的一大批骨干乐手选择了离开,陈佐湟也辞去了艺术总监一职。“很多事情,已经离音乐和艺术太远了……要想让一种外来艺术在中国发展到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不是4年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有钱、有好的乐器、有几个技艺超群的音乐家就可以做到的,它还需要其它的文化因素和大的环境。急功近利的态度并不利于这个事业的发展。”类似的话,陈佐湟一直在说,他不怕把自己置于漩涡之中,在音乐界,他愿意当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如今,当初的困惑、无奈早已淡了,但坚持还在。他对记者说:“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位置。中国交响乐最辉煌的时刻,或许是在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后,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最终可以攀登到最高峰而铺路。”
2007年,陈佐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受邀出任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大剧院在天安门和大会堂旁边,对面就是中南海,处在一个很敏感的地方。”但他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个位置,让国家大剧院在国内外艺术版图中的地位得到格外的凸显。
2007年4月,到国家大剧院报到的第二天,陈佐湟就拉着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开会,提出办一个“中国交响乐之春”,让那些一辈子默默耕耘的音乐家们能到大剧院音乐厅开一个音乐会;2007年夏,他在全世界同行的惊诧目光中,只用3个月时间就办起了别人要用3年才能筹划完备的演出季,将全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乐团都请了过来;2008年3月,他坚持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了大剧院管风琴音乐周,让更多人领略“殿堂之音”的美妙大气;2010年3月30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乐团的72名年轻乐手是他带领工作人员从全世界1000多人中挑选出来的……陈佐湟说,到国家大剧院的最初三四年里,他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艺术定位,想尽办法让大剧院在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演出市场上被认可。“这或许是我能给大剧院的最大贡献。一个剧院最终能走多远,和第一代人的关系特别大,如果现在不把这个事情做好,把根基扎稳,以后就没谱了。回头想想,还好,我们基本上做到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是陈佐湟在采访中总挂在嘴边的话。而他人生的每一步,就是在责任的牵引下一路坚持下来的。“也许是年龄越来越大,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比原来更多。”他对记者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每一代人都认识到了这种责任,都认真地去做了,民族才有进步的希望。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没有旁观,全部都参与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