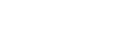6月20日从杭州出发,经过兰州、敦煌,从柳园进入乌鲁木齐,游天山、喀纳斯湖,后乘火车去伊宁,从伊宁去看了在霍城的伊犁将军府,察县的锡伯族历史博物馆,霍尔果斯口岸,然后从伊宁去了著名的八卦城特克斯,从特克斯去昭苏看了赛马节,后从特克斯去了新源,从新源乘汽车途经那拉提到和静,从和静又乘火车到阿克苏,再从阿克苏到喀什,在喀什去瞻仰了香妃墓,参观了艾提朵尔清真寺,然后去了和田,再从和田回到乌鲁木齐,去了乌鲁木齐附近的五家渠,7月26日,乘火车从乌鲁木齐返回杭州。近40天的旅行,大致游历了南北疆,对中国之大有了实际的感受,原生态的山川湖泊已经刻入我的脑海,永远也无法抹去;同时,也对目前新疆的民族问题有所见闻,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在乌鲁木齐,汉族出租司机告诉我们,2009年七五事件以后,我们的心伤了。从这句话,我体察到其实居住在新疆的汉人,内心是喜欢维族人的,抱着同样的感想,我7月25日与新疆大学中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孟楠教授约见,他明确向我披露了希望达成汉维和解的意愿,这也证实了我的感想。从新源到和静的盘山公路十分险峻,买车票时,售票员让我们买了保险,开车的司机和副司机都是维族人,一车人中汉族居多,也有回民,都能放心让维族人开车,把生命交给了他们。可见,在新疆汉维之间并无隔阂。
在喀什,我看见维族人围坐在街边的毡垫上,吃老汉瓜的场面,十分祥和,他们的坐姿与在清真寺的坐姿相同,接近于日本人的正坐。维族、哈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在毡房中,也是盘坐在桌几前生活的,与日本人的家居生活相似。对照我所了解的日本人的生活,我对新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产生了同情的了解。
我们从柳园车站坐车去乌鲁木齐是6月26日,在安检时,我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被公安人员收缴了,没有一纸凭证,似乎理所当然,到了乌鲁木齐才知道这天鄯善发生了暴乱。后来知道,和田相继发生了暴乱,看到(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会见维族民众,提倡民族融合的报道,心里感到些许安堵。在和田,农村来的维族出租车司机不懂汉语,但和田城里的维族人多会汉语,对我们十分友善,汉维两族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十分自然,并无异样。
处处都要安检,带着红袖章的安全员也随处可见,武警的车队,甚至飞机的巡逻或许也有某种威慑效果,但我觉得,维族人的日常生活依旧,在湖边与绿荫下,可以看到维族人的情侣与家人在嬉戏。7月的封斋期间,穆斯林似乎更加热衷于在清真寺做礼拜。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甚至还影响到了中亚邻国。
在平静的外表下面,也必须承认汉维之间的“民族”裂痕仍在蔓延。我在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列车上遇到一位中学教师母子,他们是石油工人的家族,居住在泽普,原籍是甘肃。女教师告诉我,在新疆出生的儿子羡慕甘肃老家的同龄孩子,因为那里没有民族争纷。我听后,感到一阵心酸,汉维之间的不睦已经开始影响到了下一代的生存环境。一位曾在和田任教的中学数学教师,也因感到班里民族学生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要求调到乌鲁木齐去工作了。他们都是新疆人,生活在新疆这片美丽迷人的土地上,更加感到民族不和的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和并无谁胜谁负可言,社会为之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需要保卫新疆的社会,恢复受到伤害的汉维两族间的信任关系。
究竟谁是汉维冲突的元凶?学术界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要接受苏联民族政策的教训,但事实上,苏联的解体缓解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压力,而中共从苏联邦解体中得出了需要强化国家权力的“教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改变了从前汉维相安的社会关系,压缩了汉维在新疆相互合作的社会空间。新疆汉人被一部分持极端主义立场的维族视为眼中钉,维族也被一部分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汉人视为异己分子。这样,本应该携手共建新新疆的新疆人,就被人为地划分为汉族与维族的对立构图。元凶恐怕还是中国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没能跟得上民族国家的建设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