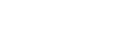我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记忆
作者 殷宗毅

作者 殷宗毅近照
从我记事以来,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四.五事件”和“打倒四人帮”等政治运动,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我们家的每个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这场“政治劫难”中都饱受了创伤。现在那场“政治浩劫”已经过去了许久、许久......我早已没有了任何的埋怨和仇恨,只是想把那段特殊年代里,自己当时所亲历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而已。同时希望像那场的“政治浩劫”再也不要发生了,让我们的国家在休养生息中繁荣昌盛,百姓们永远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每当回想起“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段痛苦的记忆,我心里都是格外的沉重和疼痛。那时候的人们简直像疯了一样,成天以整人为乐趣,今天整倒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倒,好像不整人就过不得一样地循环着。
我父亲于1928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南充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里,家里除了舅公张澜先生是民主同盟会的创始人、爷爷殷世杰先生是黄埔军校六期炮课毕业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我父亲是中共党员干部外,其他众多的亲戚都是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我母亲于1935年2月,出生在山东省潍坊的一个农商兼有的满族大家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父母亲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先后离家参军入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父亲因政治上的问题(父亲当时被定为“彭德怀分子”),部队医院工作的母亲便跟父亲一起,从部队上被下放到兵团农一师胜利渠管理处(后称农一师沙井子灌区管理处)了。当时农一师胜利渠管理处的处长是农一师副师长冯海英伯伯兼任,我父亲在管理处担任党委委员兼工作员,妈妈则安排在胜利渠管理处卫生队做助产士工作。没多久,父亲考入了刚成立的“新疆八一农学院”,在经济管理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就读,也是这个学院成立以来的首批学员。大学毕业后,父亲又被分配回到了胜利渠管理处(后称沙井子灌区管理处,或农一师第一管理处)工作。不久,父亲调到了新成立的农一师十七场工作,任十七场的经营管理股股长。很快,说父亲是“彭德怀分子”和有“经济问题”,被撤职下放到农一师第三管理处(即后第三管理处与十六场合并为农垦十三团,以下简称三管处)干部队劳动锻炼。

1960年8月,在我出生没多久,父亲调到了农一师十六场工作,担任十六场的经营管理股股长。
在我妹妹出生的第二年秋天,妈妈把已63岁的姥姥接到了新疆。姥姥是个满族人,她老人家那时带着我年幼的小姨姨,生活在山东省潍坊老家。当地政府虽然按军属对待,但姥姥因常年体弱多病而难以照料。
1965年夏天,父亲被下放到了十六场基建二队任指导员。
我记得当时团场的整个作息方式,仍然按照部队的管理方式和习惯。每天早晨听到连队的有线广播里播放起床号声后就起床,人们在后面播放的《国内外新闻简报》中,起床、洗漱和整理家庭内务。二十分钟后,连队的食堂就敲钟开饭了,大人们纷纷拿着碗筷到食堂排队,凭票打卡吃早饭。食堂的早饭一般是:每个人一个四两的玉米窝窝头(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次白面馒头),一碗玉米粥和一点炊事员自自己炒制过的咸菜。在大家吃饭的时候,连队的主要领导就在现场开始安排今天一天的工作了。待吃完早饭,大人们把碗筷送回到家后,便纷纷拿着劳动工具开始上班了。中午,由食堂炊事员将午饭送到劳动工地上,大家凭票打卡打饭吃。中午饭是:每人一个四两的玉米窝窝头(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次白面馒头)、一勺有点荤腥的炒菜(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次到肉),偶尔还可以喝到一点菜汤(也就是洗锅水加点盐)。下午(经常是晚上),听到广播里播放下班号声了,大人们则扛着劳动工具回到家里简单的洗漱后,就到食堂排队和凭票打卡吃晚饭。晚饭吃的与中午饭差不多(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次白面馒头和肉)。一个小时后,在当天带班领导的哨子声中,大人们全部集中到连队的大礼堂里,开始为期两个小时的晚间政治学习了。
那个时候,每家每个月的口粮、食油(即棉籽油)、食盐和肥皂,都是拿着购粮薄到连队事务长那里按定量领取,月底统一按定量标准结算扣款。超出的部分和其它像糖、牙膏、烟和酒等,则要在连队事务长去那里按规定的定量溢价购买。蔬菜按家里人口多少,一个星期分两次。猪肉也是按家里人口多少,一、两个月才能分到一次(每家分的肉上都贴有名字),每次每人顶多也只能分到200—300克连皮带骨的猪肉。到了瓜果熟了的时候,也是一个星期才能分到一次,但在最后一次分苹果、梨子和瓜的时候,大家都会先把苹果、梨子和瓜晒一晒,然后在菜窖里储藏起来慢慢吃,一直可以吃到来年的二、三月份呢!所以,在春夏时节,家里有上学的孩子,则在的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外出打青草回来喂鸡。因为那时每家还允许喂5—6只鸡,但不准多喂,其它家禽和家畜则不允许喂。如果发现多喂了鸡和喂其它家禽,是要被开“批斗会”和进学习班“学习”的,多喂的鸡和其它家禽也要被抓走充公。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啦!
顿时大家都人心惶惶的,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增加什么人,被作为新的运动对象挨整批斗了,至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这几类人在每次运动都跑不了。连队的整个作息方式和时间虽然没有变化,但作息时间里播放的音乐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起床号变成了歌曲《东方红》。半个小时后,大家在歌曲《敬爱的毛主席》声中,集体排好队一起跳“忠字舞”。跳完“忠字舞”后,在广播播放《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时候,大家对着写有《毛主席语录》的语录碑排好队,向毛主席进行“早请示”。随后,在广播播放《红旗》社论文章和《国内外简要新闻》的时候,大家到食堂排队和凭票打卡吃早饭。这时候的早饭只是:一碗玉米粥、一个四两的玉米窝窝头和一点炊事员自己泡的咸菜。吃完早饭后,大家迅速把碗筷送回家,赶紧拿着劳动工具开始上班了,连队的有线广播才停止播放了。到了中午,广播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时,食堂炊事员才能把午饭送到劳动工地上给大家吃。中午饭是:每人一个四两的玉米窝窝头(一个星期才能吃到一次白面馒头)、一勺有点荤腥的炒菜(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次肉都很不错了),偶尔能喝到一点菜汤(也就是洗锅水加点盐)。在接着的“八个革命样板戏”选段播送完后,就开始了下午的生产劳动。晚上听到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大伙们下班则要排着队回到连队的篮球场,待连队当天的带班领导把今天劳动情况讲评完后,才能回家里洗漱、到食堂排队和凭票打卡吃晚饭。晚饭每人还是一个四两的玉米窝窝头、一勺有点荤腥的炒菜(一个月可以吃到一次到肉),偶尔能喝点菜汤(也就是洗锅水加点盐)。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大家又要集中到连队的篮球场,在播放《敬爱的毛主席》的歌曲声中,开始排队集体一起跳“忠字舞”。“忠字舞”跳完后,大家还要排队对着《毛主席语录》碑,集体向毛主席进行“晚汇报”。休息半个小时后,由连队当天的值班领导吹哨子,召集大人们到连队的大礼堂里,开始为期两个小时的晚间政治学习。
跳“忠字舞”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就停了下来。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紧张气氛和情况,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才开始有所缓解和改变,但劳动生产的轮休制并没有多大变化。每到春耕、中耕、收获(割)和大渠和排碱渠清淤(泥) 的时候,七天的轮休制就改为十天轮休制,好像一年四季总是处在“农忙”的状态,根本没有多少天在休息一样。
196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突然来了三个造反派带了十几个红卫兵,冲进我们家就直接到处乱翻,说我父亲是“彭德怀分子”、“保皇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家里肯定藏有“彭德怀交给的文件和材料”,限我父亲必须在36个小时内,将这些所谓的“黑文件和材料”都交出来,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把父亲押走。经过一天的折腾,除了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件和父亲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学习期间用的书籍及资料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翻找出来。第二天他们又继续“挖地三尺”式的进行翻找,把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有关彭德怀的“文件和材料”早被妈妈包好埋在菜窖里了)。第三天一早,造反派和红卫兵就把父亲捆绑着,押上汽车就拉走了。当时,母亲和姥姥(即外婆)看到父亲被他们用汽车拉走时,像疯了一样地追赶着汽车。当妈妈在看清了汽车的去向后,连忙让姥姥(即外婆)带着我年幼的妹妹(当时妹妹还不到3岁)守好家,自己则骑上自行车带着我赶到了场部,找到了当时军管会的李政委问明情况,才知道是军管会按“彭德怀分子”、“保皇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抓走和关押了我的父亲。母亲知道了父亲被抓的缘由和关押的地方后,又急忙把我安顿在了父亲的好友高振武伯伯家里(因为高振武伯伯是个老红军、又是十六场分管机修的副场长),自己则在天黑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赶回了家。
没多久,造反派和红卫兵开始用汽车拉着父亲,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各个单位巡回开批斗会了。就在造反派和红卫兵拉着父亲来到基建二队开批斗会的时候,妈妈正好刚把我接回到了家里。当造反派和红卫兵把父亲押进连队的大礼堂后,要求我们全家马上一起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批斗会一开始,我看见造反派和红卫兵先把父亲用绳子五花大绑的向后绑着双手,脖子上挂着写有“打倒彭德怀分子”、“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打倒地主孝子贤孙”和“打倒国民党残杂余孽”等罪名的大牌子,牌子底下还分别吊着两块各重十公斤的拖拉机链轨板,头也被理成了光头。爸爸被造反派和红卫兵一押上主席台,马上叫妈妈到台上与父亲站在一起陪斗,叫姥姥、我和妹妹站在台下第一排看父亲怎么被批斗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来参加父亲批斗会的人三三两两的,就是来的人也都是没精打采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在稀稀拉拉的口号声中,宣布了批斗大会开始。他们先历数了给父亲罗列的所谓“反革命罪状”,然后逼迫着父亲自己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父亲则先历数了自己从小长到大的经历,又讲了自己参加革命后所干的工作后,就什么也不说了(因为涉及保密的东西是不能说的,这是组织纪律)。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一个造反派负责人,连续问了我父亲几遍:“还有呢?”,便冲到父亲的面前连打了父亲几个耳巴子,嘴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什么。父亲当时被打的满嘴是血,牙齿也打掉了一颗,立刻引起了台下许多群众的不满,而妈妈只能站在一旁低着头无助地默默哭泣着。造反派这时开始点名叫人上台来控诉父亲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可台下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们。看到父亲在台上被人辱骂和殴打,我当时又急又气,真想冲上台去帮父亲一把,可手臂确被姥姥紧紧地抓住,一点也动弹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亲在台上受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一会儿,秦积民和赖志军(我非常感恩这两位兄长!)两位哥哥悄悄地把姥姥、我和妹妹拉出了会场,让我们到连队的大菜窖(用于冬天储藏过冬菜的)里先藏了起来。过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赖志军哥哥又跑过来,找到我们说:“因为中午没人管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饭,批斗会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散场了,造反派和红卫兵又用汽车把你父亲拉走了,你妈妈现在已经回到了连队的医务室,正等你们回家呢!”于是,姥姥领着我和妹妹到了连队的医务室,找到妈妈就回家了。和妈妈一起回到家里,我看见妈妈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神情非常的沮丧,两眼红肿,头发也有些凌乱。妈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告诉姥姥:自己有可能不久也会被关进“牛棚”里,要姥姥坚强些,带好我和妹妹。一个星期后,妈妈就被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带走关进了“牛棚”,家里只剩下了姥姥、我和妹妹三个人。后来,听父母亲说:在刚关进“牛棚”的时候,每天白天要参加开荒造田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则在打骂声中,边开自己的“思想斗争会”,边写自己的“交代材料”,一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三个月后,白天还是要干重体力劳动,晚上只是写自己的“交代材料”了。在父母亲被关押到“牛棚”的日子里,其他人经常一见到我,就乱骂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有时还无缘无故地打骂我,让我也低头认罪地交代父亲的“罪行”,甚至还把我拉到《毛主席语录》碑前,逼着我背诵《毛主席语录》中的“老三篇”,背不出来他们就打我一顿。我现在的“记忆力好”,就是那个时候被“磨炼和锻炼”出来的。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也下的特别大,我不小心还得了一次雪盲症呢!是我的小学恩师孟秀莲老师,用她自己的奶水给我及时医治好的。我至今从内心里都十分感恩这位恩师!
虽然,父母亲先后被关进了“牛棚”,但连队给我们家的粮食、油、盐、布票和肉还都能按时按量的供应,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每天家里担水和劈柴的活路,就落在了我这个才7岁多一点的孩子身上了。因为姥姥是个近七十岁、又是“三寸金莲”小脚的老太太,自己走上个几百米都非常困难。所以,每天下午放学回到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马上要去距离一公里半远的地方,靠近南干大渠边上的井里去担水,去晚了井里的水就成了泥水汤汤,根本就喝不成了。当时因为我年龄太小,姥姥就让我挑水时,在前面挑一个能装八公升水的铝质水桶(此铝制水桶现在还保存到的),后面挑着一个能装三公升水的铝质茶壶。第一次挑着空桶和空茶壶去担水,由于找不到扁担的平衡点,在去挑水的路上总是跌跌撞撞的,等快到挑水的地方时,我已经走的轻松自如了。第一次从水井里往外打水,有大人先帮我把三公升水的铝质茶壶装满水,又帮着把八公升水的铝质水桶装了半桶水。在挑着水往家走的路上,我又因找不到扁担的平衡点而行走的跌跌撞撞,走上二、三十米就要休息一下。待休息了二、三次后,我也就行走自如了。可回到家中,发现两个小肩膀都已压得红肿了,好疼啊!......
记得冬天一次我去挑水,好长时间没有一个大人和哥哥姐姐们来挑水,我只好一个人面对着扑满厚厚冰碴子的井口发呆。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来,我就麻着胆子提着水桶从冰上走到了井口台前,试着把水桶的提把挂在打水链子的铁钩上,慢慢地把水桶放进了井口里。待感觉到水桶里装满水后,我就用尽全身力气地摇辘轳。当把水桶摇到井口时,我赶紧去抓水桶的提把。可能是因为心太急,天也太冷,我的一只脚当一不小心就滑向了井口,要不是被人急忙抓住,我当时肯定掉进了井里啦!当我回头看看是谁拉了我一把时,才发现是彭大魁哥哥(彭秋菊姐姐的哥哥,非常感恩!!!)救了我,这时我的内衣内裤都被冷汗浸透了。从那次以后,冬天里每次到井里挑水时,我都心有余悸,非常害怕一个人用辘轳打水。不管天有多晚,我都一直等到有人来,请他(她)们帮我打好水,我才敢挑水回家。
后来,我不仅学会了用辘轳从井里打水,还经常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到沙漠里去(砍)背柴火呢!。
每到休息天,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到沙漠里(砍)背柴火,是件既好玩又有趣的事情。上午出发前,先要把中午吃的午饭(也就是一个玉米馒头和一小块咸菜)准备好,装进怀里捂着。然后,用军用水壶装满水,带点盐和火柴,还要带上挖柴火的坎土曼(新疆特有的一种挖土工具)、砍(劈)柴火的斧头、挑柴火的扁担、捆绑柴火和背柴火用的绳子。在去砍(挖)柴火地那片沙漠的路上,大家一会儿唱着歌、一会儿背着《毛主席语录》,而我则东张西望地慢慢跟在后面(实际上我在记回家的路)。当哥哥姐姐们发现我离他(她)们远了的时候,他(她)们就会叫我快点跟上。有时我们还偷偷地跑进玉米地里,偷几包玉米或一些土豆当中午饭吃。到了砍(挖)柴火的那片沙漠,姐姐们就开始找有露出干红柳根的大沙包,先挖出干红柳根放在一边选一选。因为好的干红柳根粗壮弯曲而不成材,木材紧实油性又大,耐烧火力旺,是烧火做饭用得最好薪柴了。有的哥哥则帮着挖干红柳根、有的就开始到别的地方下兔套子、有的去找有鸟窝的树爬树掏鸟窝、有的到塔里木河边筑坝抓鱼。到了中午时分,柴火也都挖(砍)的差不多了,哥哥们就分别陆陆续续地回来了。碰巧的话,哥哥们有的套到了三、四只野兔子或一、两只野鸡,有的掏到了很多各种鸟蛋,有的捕到了一些鱼,有的还掏到了几窝野蜂窝呢!大家就开始生火和围着火堆烤热馒头和烤玉米,同时拿出一只兔子和全部的鱼进行烧烤,把土豆埋到火堆灰里闷熟了吃。野鸡蛋和各种鸟蛋只能先用泥巴包好埋在土里,然后在土上慢慢地烧火,好将野鸡蛋和各种鸟蛋慢慢地捂熟,否则一会儿野鸡蛋和各种鸟蛋就会爆炸而吃不成了。多的野兔子、野鸡、鸟蛋和野蜂窝,哥哥姐姐们就轮流地分一点,好拿回家找人换口粮和钱,以帮补家用呢!吃完了午饭,哥哥姐姐们开始把(砍)挖出的干红柳根,用斧头劈开和截断成80—100公分左右长,堆码好后用绳子捆绑好。因为我记路的能力好些,哥哥姐姐们一般都让我背着柴火在前面带路,他(她)们则用扁担挑着柴火在后面跟着。一会儿,我就把哥哥姐姐们带出了砍(挖)柴火的那片沙漠。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又钻进玉米地里,再偷偷地掰点玉米和挖些土豆拿回家去。
快到冬天,我又跟着大哥哥姐姐们到地里“溜秋”,也就是偷偷地将地里没有收干净的土豆、甜菜(可以制作白砂糖用的块根作物)和红萝卜挖出来拿回家,偷偷地将地里未收捡干净的稻谷捡回家,帮补家里在冬天和春荒不接的粮食短缺时吃。一般“溜秋”的时间,大致也就一个星期左右。
说起溜土豆、甜菜(可以制作白砂糖用的块根作物)和红萝卜,也是件挺有趣的事。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团场各连队一般都会在瓜地的垅畦上套种土豆、甜菜(可以制作白砂糖用的块根作物)和红萝卜,在玉米地里套(间)种土豆和黄豆。到了秋末初冬时节,地面上所有的绿色都被第一次的霜冻打枯黄了,瓜地的垅畦上已分不清哪些是杂草和农作物了。这个时候,各连队因劳动力十分紧张,都会把收获土豆、甜菜和红萝卜的活路安排给女职工干。可女职工体力差,她们在收获土豆、甜菜和红萝卜时常常因偷懒而粗放,这就给我们“溜秋”提供了大好机会。在女职工将土豆、甜菜和红萝卜收获完后,瓜的藤蔓、甜菜和红萝卜的樱子也要一并清收回喂连队的牲畜。下午放学后,我就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拿着坎土曼(新疆特有的一种挖土工具)和背筐(或麻袋),乘着天还没黑就赶紧往地里跑。到了地里,先到地里垅畦中间杂草多的地方,在地面上仔细寻找到干了的土豆茎叶、甜菜和红萝卜干樱子的短茬子,然后顺着用坎土曼(新疆特有的一种挖土工具)深挖,就可以挖到土豆、甜菜和红萝卜了。有时在收获过土豆、甜菜和红萝卜的地方,也可以再溜(挖)到不少小的土豆、甜菜和红萝卜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天还没有黑透时,就可以挖到一背筐(或麻袋)的土豆、甜菜和红萝卜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以后放学了,我还会跟着大哥哥姐姐们到地里打苦苦菜,拿回家喂鸡。还学会了缝补衣服、自己制作一些简单的玩具、偷学了长拳和小洪拳(主要是保护自己),还能自觉地帮家里多做一点事情了呢!
1968年5月份,因确实查不出我妈妈有什么任何问题,就被从“牛棚”解放了出来,领导还是安排妈妈在连队继续从事卫生员的工作,但卫生室却安排了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人来当妈妈的助理(也就是来监督妈妈的)。可这时的妈妈已经又黑又瘦,每天除了正常地给人看病外,就闷闷不乐地写申述材料,有空还用自行车带我,到团里找“革委会”的领导进行申述,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
1969年7月份,父亲也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后,组织上暂时没给他安排任何工作。父亲每天除了在家里写申述材料外,就经常到十五连鸿沟(即塔里木河的古河道,作为排碱渠用)里钓鱼。我也就在这个时候跟父亲学会了钓鱼,还跟父亲学会了下兔套子和用弹弓打麻雀等。但每天在我做完作业后,父亲就要我陪他练一个小时毛笔字后,才允许我出去玩。
1969年9月,父亲被抽调到阿克苏地区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然后被分配到了新疆第一监狱(即沙雅劳改农场)指挥部担任了军管会的领导工作,我们家也随之搬到了新疆第一监狱(即沙雅劳改农场)指挥部。妈妈被安排在指挥部的卫生队,继续从事着医务工作。
1973年1月,父亲在新疆第一监狱(即沙雅劳改农场)军管会工作结束后,我们家又随父亲的调动,搬回到了幸福城(这时已改称为农垦十三团了)的学习班,父亲在那个单位担任了指导员,而我则被留在了新和县父亲战友的家里待了半年。父亲战友的一家人待我非常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紧着我先吃,我非常感恩于这家可爱的人!1973年8月份,妈妈来到父亲的战友家,把我接回了幸福城的家里。
1974年7月中旬,父亲调回到了机关工作,妈妈也被安排在机关门诊部担任内科医生。几天后,部队派专人通知父亲的政治问题(即“彭德怀分子”)已被甄别,想请父亲回部队工作,父亲说什么也要留在幸福城工作。不久,父亲担任了团党委委员兼任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负责人。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也就结束啦!
1979年7月中旬,部队又派专人来到我们家,当场宣布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即所谓的“彭德怀分子”)彻底平反了。并再次请我父亲能在“八一建军节”前回部队工作,父亲只是淡淡地说:“离开部队已经那么多年,再加上年龄又这么大,恳请部队让我转业了吧!”
1979年9月,我参加了第三次高考,考上大学后就离开了幸福城。这一年的12月份,在我们家共同生活了近17年的姥姥,因肺癌去世了,享年近80岁。她老人家生前,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人敬佩,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是那样的晓明大义,临危不乱,教会了我如何做事;是那样的贤良聪慧和勤劳,教会了我如何对待生活。我现在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啊!

作者殷宗毅